
通讯员 曾仲奎
巍巍武陵,苍山如海。亘古以来,这里,峰峦叠嶂是诗,溪壑幽谷是画,是自然造化的鬼斧神工,却也如同一道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天堑,将时光与梦想,牢牢锁在了重重大山的最深处。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习惯了在云端行走,在崖畔耕耘,他们望向山外的目光,交织着对繁华的渴望与对险途的敬畏。一条大道,承载着走出深山的百年夙愿,几代人的魂牵梦绕,终于在时代的号角声中,化作了穿山越岭的钢铁蓝图——利(川)咸(丰)高速公路。
而在其蜿蜒的轨迹上,有一段尤为险峻的征程,被标记为“四标”。这里,绝壁如削,沟壑纵横,地质构造复杂得如同大地的迷宫。测绘仪器的光标在陡坡密林中艰难跳跃,设计图上每一道墨线,都浸染着工程师们对地脉的敬畏与挑战的决心。
李子溪,这个原本宁静得只闻鸟鸣犬吠的村落,一夜之间,被推到了这场宏大叙事的风暴眼。机器的轰鸣,取代了往日的静谧,宣告着一项前所未有的变革,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叩响这片古老土地的门扉。
征途,始于足下
每一张宏伟的蓝图,最终都要落笔于大地。而将图纸上的线条,化为现实中的坦途,第一步就要在这片土地上,划开一道沉重的口子——征地拆迁。这个常被简化成冰冷数字的环节,在利咸高速四标段的每一寸土地上,都充满了血肉的温度与人情的冷暖。
小村乡征拆办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巨幅红线图。我和专班队员的战场,就在这图纸与田边地角的交界处,就在这新图与祖屋老坟的夹缝中——在每一根红线背后真实的炊烟里。
推土机还未进场,我们的脚步早已无数次踏遍标段内每一寸土地。测量仪滴答作响,评估表填了又核,而比数据更复杂的,是人的情感。
昏黄的灯光下,有老人用手一遍遍摩挲老屋的梁柱,叹息默默地抚过皱纹;即将被征用的田地头,壮年汉子蹲在那儿,一根接一根抽着闷烟,仿佛要把一家老小的生计都咽进肺里;标记了红圈的百年古树下,孩子仰起脸问:“爷爷,树要搬家吗?”
每一次丈量,都是对土地的切割,更是对记忆的剥离;每一次签约,都不只是协议的达成,更是一份对未来的承诺。
挫折,如影随形。铁门在我们面前重重关上,误解和怨言像荆棘般抽来。我们反复解释政策、核对补偿、描绘通途之后的景象。时常,磨破了嘴皮、踏穿了鞋底,换来的仍只是一声长叹、一个摇头。
那种无力感,沉甸甸的。工程一度举步维艰,有施工队扬言退场。
2023年国庆前夕,小村乡党委书记谈文才站在会议室主席台上,身后的电子屏上赫然写着百日攻坚,决胜李子溪。他声音低沉,却字字铿锵:“清零总攻——从现在开始。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
11位班子成员挂帅出征,20名干部分成7个组,责任到户。我们面对的是39栋房舍、16口水井、11个水池、27条饮水管、48座坟墓、136亩茶园……这是一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战役。
有人说,这是与耐力比拼,更是与人心较量。
深秋十月,冷雨淅沥。专班队员和评估员魏涛第十五次站在收费站坐标EK0+940的地块前。那是张家的老宅,墙板斑驳,还残留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标语痕迹。
70岁的老张蹲在门槛上,一只手长久地抚过门框,像在触摸岁月的脊梁。“这梁,是我太爷爷架的。”他声音沙哑:“那年,光绪帝还在位子上哩。”
魏涛手中的测距仪发出嘀嘀的声响,数字精确到毫米。但他明白,他测量的只能是房屋的面积,测量不了的,是老人心中那份无法用补偿价格衡量的情感。
终于在一个清冷的早晨,老张颤巍巍地在协议上按下了手印。
他说:“你们真不容易!”
他接着说:“路通了,娃们出去方便。”
最后,他语气坚定地说:“值了!”
那一刻,资料员陈颖别过脸,悄悄抹了眼角。
还有一次,工作队上门做动员,从傍晚持续到凌晨两点。主人熬不住竟然睡着了,醒来揉眼一看,干部还坐在那儿轻声解释。他嘟囔:“我都睡一觉了,你们还不下班?”
干部们只能苦笑——我们哪有什么理由下班?
“白+黑”“5+2”,成为这支队伍的工作常态。乡间夜路上,总有手电光在晃动;专班会议室的灯,常常亮到子夜。政策文件在桌上堆成小山,每一本都夹满彩色标签。
帮拆迁户抢收农作物、搬运生活物资,李子溪村支“两委”曾艳、黄莲英、刘蕾三位女性和21岁的选调生唐宇含,双手磨破了皮,洗手疼得直钻心,但谁也没有叫出声,只为多出一份力。
资料员陈颖的电脑屏上同时打开着十几个表格,补偿方案甚至精细到每棵果树的挂果期、每平方米不同作物的季产量。她甚至发明出一套“复合计量法”:除了国家标准,还加入情感系数——老宅院门的石墩、传了三代的灶台、婚嫁时栽下的合欢树等,皆被纳入补偿考量。
在一连串冷峻的任务数字背后,还藏着另一组滚烫却辛酸的数据:累计走访1352次,调处76起边界纠纷,挨过19次骂,磨破28双鞋底……
每一组数据,都是泥土中踩出的脚印,都是长夜中熬红的眼睛,都是风雨中前行的淋漓。
那些日子,专班队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我们不是一开口就谈补偿,而是先和乡亲聊子孙,聊出路,聊李子溪闭塞太久的痛。
渐渐地,临时安置点热闹起来了。邻居互相帮衬抬家具、装门窗,女人们擦拭新居的玻璃,孩子们在水泥地上奔跑笑闹。那一刻,我们眼前仿佛不是一块地、一栋房,而是即将诞生的希望。
2024年元旦即将来临,李子溪征拆工作全面清零,受到县委、县政府的特别嘉奖。没有庆典,没有表彰大会,只有一条即将动工的道路轮廓静卧于群山之间,如苏醒前的巨龙。
那一晚,谈文才在笔记本上默默写下一行字:山高不阻志,路远终可达。
所有的委屈,都在百姓一句“你们也不容易”中消融;所有的付出,都在机械轰鸣和焊花飞溅中结果。
百日攻坚,攻坚的是困难,凝聚的是人心;决胜李子溪,决胜的不只是工程,更是一个乡镇穿越风雨、走向振兴的信念。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路。它是用脚步丈量出来的民心路,是用体温焐热的希望路。
协调保障,事无巨细。工地断水断电、材料运输受阻、施工噪音扰民……桩桩件件,都需要我们如精密齿轮般,在村民、施工方和管理部门间啮合、疏通。我们成了“工地消防员”,哪里冒烟,就扑向哪里。所有的付出,奠定了利咸高速“四标”红旗标段不可撼动的地位。
这段“陪跑”,让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识到:这条路的每一寸延伸,不仅依靠钢筋与水泥,更依赖无数人用理解、包容、牺牲乃至泪水浇铸的基石。
它终将成为地图上一段平凡的线路。这条路,终将抵达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险境求通途,绝壁上的挑战
鄂西南千峰万壑,地势险要,利咸高速四标段犹如一道刻痕,嵌在近乎垂直的崖壁之上。这里是湖北省“九纵五横四环”高速公路网中“九纵”线的咽喉地段,是一场现代工程技术与自然伟力的正面交锋。
2021年,当第一批测量人员腰系安全绳悬吊在绝壁上时,他们面对的是一张“白纸”——施工便道需在无路可循的峭壁上凿出59公里“生命线”;马家井隧道悬于峡谷半空,连找个站稳脚跟的地方都是奢望。建设者们自嘲:“修路队变成攀岩队啦!”
打开四标段施工图,一组数字令人窒息:81.3%的桥隧比,意味着近16公里的路段中,桥梁和隧道超过13公里。5座桥梁、5座隧道、10段路基和1处互通——这不是普通的高速公路,而是中国山区基建的极限挑战。
“哪是在修路,分明是在雕刻群山。”工区经理罗德站在田福湾隧道口,身后的岩壁不时传来沉闷的爆破声。2024年初春,他指挥着200多名工人同时在多个作业面奋战,每一个动作都在与工期节点赛跑。
马家井隧道地质勘探报告读起来像一本惊悚小说:施工区域属构造侵蚀剥蚀中低山地貌,Ⅳ、V级围岩占比100%。这类岩体如同压紧的沙堆,一遇扰动就可能塌方。在田福湾隧道深处,最大埋深达389米的地层压力,让每一米掘进都变成一场生死博弈。
隧道内,湿热的空气混杂着柴油和岩石粉尘的味道。开挖班班长方德文紧盯着岩壁,手中的探灯仔细扫描着每一寸新暴露的断面:“你看这些裂隙,像是大山的血管,我在它的血管里打洞。”突然,一阵细碎的落石声让他猛地抬手:“停!退后!”工人迅速后撤,几分钟后,一块桌面大的岩石轰然坠落——这只是日常工作中最轻微的“警告”。
每当夜幕降临,工程一线指挥部的灯光星星点点。中交二航局项目经理部经理谭小艺手指划过设计图上那些代表桥梁和隧道的密集标记,语气凝重:“这每向前推进一米,都意味着是在大山的心脏上动手术。”
在两洞桥工地,工人们悬在近60米高的塔吊爬梯上作业,峡谷的风像无形的手推搡着他们的后背。安全员吕晓龙的对讲机从不离手,他的眼睛始终追踪着每一个作业点:“在这里,一阵大风、一场急雨都可能致命。我不仅要计算混凝土的强度,还要计算风的脾气、雨的性子。”
技术创新成为突围的关键。项目团队研发了基于微震监测的围岩稳定性预警系统,像给大山做“心电图”;采用无人机进行高精度测绘,绘制出毫米级的地形模型;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喷浆机械臂,让最危险的初支作业效率提升三倍。
2024年“五一”,1000余人集体留守。群山间灯火彻夜不熄,像给大地强行缀上了陌生的星座。金属撞击声、马达嘶吼、人的号子,这些工业文明的噪音刺破了山鬼与林精的耳朵,五天超千万元产值,每一元都浸着隔夜的凉汗与无法预知的伤亡。
最艰险的施工段,工人要顶着45℃的高温作业,汗滴在钢模板上瞬间蒸发。测量员每天负重20公斤仪器攀爬70度陡坡,GPS信号时断时续,他们就用手工测绘填补技术盲区。
2024年10月,当最后一段隧道贯通时,爆破声惊起山鹰,而建设者们只是沉默地击掌——所有的艰辛都化作混凝土里的分子,永远凝固在这条山脊线上。
中交二航局项目经理部的墙上,“毫米级误差决定生死”的标语下,是一张巨大的倒计时牌和更巨大的工程进度图——红色代表未完成,绿色代表已贯通。每一天,工人们都在用汗水和智慧,将红色一点点变成绿色。
在这片曾被标记为“筑路禁区”的峡谷中,建设者们正在完成一场现代版愚公移山。他们凿穿的不仅是433米深的岩层,更是工程技术的极限;他们架起的不仅是跨越峡谷的桥梁,更是连通未来的通途。当通车之日,车辆飞驰而过时,乘客或许不会注意到窗外绝壁上那些细微的“雕刻痕迹”——但那每一个痕迹里,都镌刻着人类与自然对话的勇气与智慧。
崇山峻岭间,这场雕刻群山的壮举仍在继续。每一次爆破的回声,都是向大山深处进发的号角;每一米掘进的背后,都是工程技术与人定胜天信念的双重胜利。在这里,路不仅是路,更是人类意志力的延伸,是文明与自然博弈后达成的和解。
云端筑路,59公里便道托起16公里天路
从小村集镇转入施工便道,车辆猛地扎进仅容一车通行的施工便道——这不是道路,而是悬于天地间的绳索。车辆在悬崖边缘颠簸盘旋,右侧车窗紧贴嶙峋峭壁,左侧轮距悬崖不足半米,俯首可见云雾在百米深谷中翻涌。海拔跃升1000米后,终于抵达李子溪村田福湾隧道口。驾驶员总要摇下车窗,深深吸一口带着炸药与柴油味的山风——这不是诗意,而是劫后余生的仪式。
这段令人头晕目眩的旅程,是建设者每天的必经之路。
四标段主线仅15.96公里,却需修建59公里施工便道,相当于主线长度的3.7倍。这些盘绕于峭壁间的“毛细血管”,连通了小村、唐崖、沙溪3个偏远乡镇,运送着近千名工人和数十万吨建材,每道车辙里都浸着汗水与坚守。
材料运输是一场西西弗斯式的苦役。数百万吨建材,依靠这59公里“毛细血管”一吨吨喂入大山的脏器。卡车如蚁行,在悬崖边缘战栗、颠簸、盘旋,引擎哀号如同肺痨患者最后的喘息。
运输之难,如鲠在喉,数字背后藏着更惊人的现实。这些缠绕在茫茫大山的“毛细血管”,每延伸一米都要与六七十度陡坡搏斗。
“为一座桥墩修一条便道”,在两洞桥大桥工地,运输难度达到极致。在深达百米的“V”形峡谷中的两洞桥大桥工地,建设者甚至要在绝壁上凿出作业面。站在谷底抬头仰望,两侧岩壁如刀劈斧削,建设者仿佛成了攀附在绝壁上的蚂蚁。空压机的嘶鸣在山谷间碰撞回响,电焊弧光在云雾中明明灭灭,测量员腰系安全绳悬空定位,爆破工在烟尘中开拓着毫米级的进展。
当第一车水泥历经七道转弯才送达马家井隧道口时,测量员潘周全在日记本上颤抖着写下:“深谷回响引擎声,便是希望的声音。”然而希望是个太过文明的词汇,现场拥有的只是动物性的执着。工人们用肉身对抗地质年代,血珠混进混凝土,即刻被碱性与时间吞噬,留不下任何英雄主义的痕迹。他们谈论孩子的学费、女人和酒,唯独不谈恐惧——那玩意儿像汗一样出多了会脱水,必须吝啬。
中交二航局项目经理部经理谭小艺站在两洞桥的合龙处,风从谷底呼啸而上,安全帽带子抽打着他的下颌。他俯身摸了摸还带着温热的桥面,突然想起第一车水泥运抵时的鸣笛——那声响竟如远古巨兽的怒吼,野蛮地划破了鄂西南山区亘古的寂寥。
这是基建狂魔对天堑地壑的一次凌辱性征服。
夜幕初上,焊花再次点亮峡谷。便道上的车灯渐次亮起,在山脊间连成一条闪烁的银河。明天,这些毛细血管仍将输送着希望,直到天堑终成通途——在层峦叠嶂的绝壁深处,现代愚公们正在用钢铁与意志,重写大地的基因。
回溯至便道初拓时,测量员徐周顺的红布条在荆棘丛林里失了颜色,差点迷失了方向。推土机像一头愤怒的困兽,对着喀斯特地貌的石灰岩壁发出无奈的嘶吼。当地向导摆手说“这路神仙不过”,工人们便从牙缝里挤出笑来,将柴油灌入机器,开始了机械对岩石的肆虐。于是,“之”字形的伤痕盘绕山体而上,像受刑者背上的鞭痕,新鲜、粗粝、冒着土腥气。便道狭窄仅三米,外侧车轮距深渊常不足一掌,内侧岩壁则不时落下些诡谲的赠礼——碎石、断枝,甚至是一条碧绿的毒蛇。
“鄂西南山区施工难度不亚于贵州。”中交二航局项目经理部书记冯辉感叹道。这是行业内的黑话,意指这是又一处吞噬预算、时间和体力的无底洞。这句感慨背后是12处高边坡地灾点,是45度温差挑战,是上百次抢险保通战役。
当马家井隧道终于贯通,当两洞桥大桥真正合龙,那些盘旋于峭壁上的59公里便道——这些曾作为“血脉”的临时器官,将迅速被遗忘。它们会被荒草啃食,继而被风雨销蚀,最后彻底归还于寂静。无人再记得车轮曾如何碾过生死边缘,只有那16公里“天路”永存,作为文明的勋章,亦作为自然被人类又一次征服的见证。
那些在夕照下如一道道鞭痕的便道,蜿蜒于墨绿的山体上。天路终成,便道已往,而深谷中将永远回荡着曾经的引擎声声。
穿山越壑:田福湾隧道的560个昼夜
2024年5月2日10时,大地深处传来一声沉闷的震颤。这不是地震,而是胜利的轰鸣。烟尘尚未散尽,强光灯已刺破昏暗,映照出数张激动得发红的脸庞——来自隧道两端的施工人员同时摘下安全帽,相视而笑。右幅隧道以不超过20毫米的误差精准对接,犹如失散多年的兄弟紧紧相拥。这一刻,距离首批建设者进驻工地,已过去560个日夜。
“贯通误差17毫米!”测量工程师景伟嘶哑的报数声通过对讲机传出,现场瞬间沸腾。毫米级的胜利,是16个月来每时每刻的精密计算与严格控制。
左幅隧道的提前贯通绝非仅仅是进度表上的数字。它意味着马河大桥T梁架设的运输命脉被打通——每片重达80吨的T梁可以通过隧道直接运抵桥址。
张师傅的卡车停在新贯通的隧道口,驾驶室里放着吃了一半的盒饭,“以前一趟要两个多小时,现在只要15分钟!”
在隧道深处,焊工老聂的面罩下闪着蓝色弧光。560个昼夜,他焊接了超过5公里的焊缝,“每道焊缝都要经得起百年考验”。
“这里是施工最难啃的硬骨头”,地质工程师指着一段斑驳的岩壁介绍。工人们采用超前地质预报和管棚支护相结合的方式,一寸寸地向前推进。岩缝中残留的钻头断齿,成为这场战斗的永久见证。
夕阳西下,庆功宴的欢笑声在山谷回荡。田福湾隧道如同一条钢铁脊梁,深深嵌入雄奇大垭门的山麓,见证着人类智慧与自然条件的精彩对话。车轮碾过尚带温热的混凝土路面,驶向又一段待凿穿的险峰。
项目经理谭小艺的办公桌上,放着厚厚一摞施工方案,边角都已磨损发白。最上面那份《田福湾隧道专项施工方案》封面上,有人用红笔写着:“精度决定深度,态度决定高度。”在560个昼夜里,他们用坏钻头1872个,消耗焊条48吨,浇筑混凝土15万立方米——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建设者们用热血书写钢铁脊梁诞生的传奇。
如今,贯通后的隧道成了天然的“地质博物馆”。不同岩性的断面犹如千层糕被钢筋混凝土包裹,记录着与每片破碎带搏斗的痕迹。当第一辆汽车驶过隧道,灯光将刺破沉积千年的黑暗——筑路者的足迹已隐入大地,唯有长桥卧波、通衢连嶂,诉说着人与山海的永恒对话。
这条嵌入大山动脉的钢筋混凝土腔体,不仅刷新了利咸高速隧道施工的精度纪录,更成为测量人类意志力的标尺。通车之日,当首批车辆穿行其间,谁也不会看见岩缝中残留的钻头断齿,但山体会永远记得——那些用毫米计算胜利的日夜,如何锻成通往未来的坚盾。
夜色中的田福湾隧道如同一条发光的长龙,静静地卧在群山之间。未来的某一个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射在隧道口时,将有无数车辆穿过这条用560个昼夜铸就的通道,驶向更远的远方。而建设者们早已转战新的工地,继续在群山之间书写下一个穿山越壑的故事。
在“豆腐”里打洞,马家井隧道的生死攻坚
2024年8月28日,当最后一层岩壁在爆破中崩塌时,马家井隧道右幅透出咸丰一侧的天光,四标段最艰巨的挑战被攻克。工人老李抹去满脸岩粉,对着贯通点大喊:“咸丰,我们来了!”声浪在洞壁间回荡,21个月的艰辛随这声呐喊倾泻而出,参建者们红着眼眶相拥。
测量主管马保军反复核对坐标后,突然摘掉安全帽深深鞠躬——贯通误差仅27毫米,达到铁路级精度标准。
这不仅是地质的挑战,更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终极博弈。
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马家井隧道牵动人心。这座分离式隧道左幅4575米、右幅4515米,最大埋深433米,穿越利川与咸丰交界的高山峡谷。
2021年初冬,当队伍开进群力村时,眼前景象令人窒息——洞口悬于百米峭壁,下方激流奔涌。项目经理谭小艺攥紧图纸的手渗出冷汗:莫说施工,连找块立足之地都是奢望。
面对洞口无作业面、水资源匮乏、电力不足等难题,建设者通过改移河道、填筑河谷等方式开辟施工场地,在隧道旁开挖蓄水池,铺设专用电网,誓言啃下这块“硬骨头”。
“改河造地!”专家会议上,总工程师王艳琴掷地有声的决策让全场鸦雀无声。这个大胆的设想意味着要在汛期前完成河流改道:先在激流中筑起围堰,将河水逼入新开挖的导流渠,再用3万立方米填料夯平旧河床。测量员们腰系安全绳悬吊在峭壁间布设控制点,爆破组在涨水前抢炸出导流渠轮廓。最惊险的围堰合龙阶段,20台抽水机连续运转72小时,工人们站在齐腰深的冰河里加固钢笼。百日奋战后,奇迹终于出现——曾经被深渊吞噬的河谷上,崛起了一座足有两个足球场大小的施工平台。
然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隧道掘进至K78+64桩号时,地质突变导致浅埋段突涌爆发,岩浆如泥石流般以每小时600立方米的瀑流从掌子面喷涌而出,抽水机被冲得七零八落。抢险队长董吉勇带着“党员突击队”顶着冰冷的水柱抢装排水管,工靴里灌满泥浆,每个人的嘴唇都冻得发紫。更可怕的是岩爆——当掘进到高地应力区时,积蓄了亿万年的岩层应力瞬间释放,碎石如子弹般喷射,安全帽被砸出白痕。项目部紧急引进德国制造的长臂挖机,操作手坐在防弹驾驶室遥控处理危岩;岩壁上布设的微震监测系统24小时捕捉应力变化,成功预警了17次重大险情。
马家井隧道绝非寻常工程,隧道穿越的地质条件堪称“地狱模式”——100%的Ⅳ、Ⅴ级围岩。这种岩体遇水即化,强度极低,用工程师的话说,“好比用筷子插进豆腐里,稍不留神就会前功尽弃”。
最大埋深433米的地层压力,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隧道支护结构承受着每平方米数百吨的压力,洞顶坍塌风险如影随形。项目总工王艳琴形容每次掘进“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监测数据稍有异常,整个工作面就必须立即撤离。
一天,支护班长老洪摩挲着钢拱架上渗出的水珠。他身后,湿喷机械手正争分夺秒给洞壁喷涂混凝土,水雾在灯光下泛起虹彩。这片被地质报告标注为“极不稳定”的岩层,每天最多推进2.4米。工人们戏称自己是在“毫米之间抠生命”,每寸掘进都伴随着13项实时监测数据的跳动。
技术员小吴的监控室里,岩体CT扫描图铺满整墙。“昨天还是四级围岩,今早就变成五级围岩了。”他指着屏幕上突然出现的蓝色阴影——那是未探明的地下含水带。如何以硬核手段攻克“变脸软岩”?项目科研攻关小组给出答案。
应急响应立即启动:注浆班组带着特制双液浆赶赴现场,地质工程师视频连线成都专家会诊,洞内作业面在13分钟内完成疏散。这种惊心动魄的拉锯战,在过去18个月里上演了27次。
科技利剑破困局,面对挑战,技术团队祭出了一套精准的“组合拳”。每天开工前,超前地质钻探就像工程的“CT扫描”,通过30米长的钻芯样本精确探明前方岩层状况。地质工程师们则拿着记录板,对掌子面进行“地质素描”,任何细微的岩层变化都被实时记录分析。
“看,这里的节理面开始渗水了!”身为高级地质工程师的罗德发现异常后立即举手叫停。湿喷机械手随即进场,以每分钟喷射8立方米混凝土的速度快速加固洞壁。这些机械臂如同灵活的医生,在创面上精准“敷药”,让脆弱的岩体瞬间获得支撑力。
在已完成初期支护的段落,应用智能信息化二衬台车、湿喷机械手、半自动挂布台车等智能设备,有效提升了隧道施工质量与效率。操作手老蒯精准控制着防水卷材的铺设,接缝误差控制在毫米级——“隧道百年大计,防水是关键一环,我不允许任何瑕疵。”
“管超前、弱爆破、强支护、勤量测、早封闭”——这十五字方针被制成巨幅标语悬挂在项目部最显眼的位置,更深深烙在每个建设者的心里。
“弱爆破尤其关键”,爆破专家老马指着布孔图解释,“在软弱围岩中,我们采用分段微差爆破,每孔装药量精确到克,既要保证进度,又不能扰动周边岩体。”每次爆破后,监测团队立即带着全站仪进场,上百个监测点如同隧道的“神经元”,实时反馈围岩变形数据。
2024年8月28日,右幅隧道率先贯通的那一刻,项目经理谭小艺却不敢有丝毫松懈——“右幅隧道的地质条件更复杂,我必须更加小心。”整整43个日夜,建设者们轮班作业,最终实现了精准贯通,不超过27毫米的误差,是对这些坚守者最精确的计量。
在项目现场,咸丰县高路办副主任杨朝晖指着施工图介绍:“除了马家井隧道,我们还面临白蜡湾隧道、大河特大桥、小模隧道等控制性工程挑战。”如今,这些工程节点均被一一攻克。
这条穿山越岭的动脉正在唤醒沉睡千年的群山,筑路人的号子声里,回荡着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
云中造桥:峡谷上的力学之舞
2025年仲夏,鄂西南群山深处,洞湾1号大桥的架梁现场仿佛在做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架桥机的钢铁臂膀缓缓移动,将一片80吨重的T梁精准吊入预定位置。峡谷中风声呼啸,却盖不住建设者们铿锵有力的指令声。8月16日下午3时27分,最后一片T梁稳稳落位,右幅桥面在阳光下划出流畅的弧线,如钢铁巨龙般沿着洞湾峡谷蜿蜒伸展。
“这不是在搭积木,而是在峡谷间穿针引线。”项目副经理董吉勇站在观景平台,手指向“U”形山谷深处。他黝黑的脸上刻着常年野外作业的痕迹,安全帽下露出斑白的鬓角,“每片T梁就位误差必须控制在毫米级,相当于在百米外穿针引线。”
数据显示,这座左线757米、右线759.5米的大桥需要250片T梁支撑。这些预应力混凝土构件每片长30米,相当于三辆公交车首尾相接。
时光倒回2023年9月2日的夜晚,小村互通T梁预制场内灯火通明。试验室里,混凝土试块铺满了操作台,技术人员眼底布满血丝却目光如炬。“这是全线首片T梁,必须万无一失。”试验室主任张俊指着记录本说:“我们调整了12次配合比,模拟了数十遍振捣工艺。”
凌晨4时,当第一车混凝土注入钢筋骨架时,现场鸦雀无声。振动棒的嗡鸣声中,项目总工王艳琴突然抬手:“停!第三区域存在气泡聚集。”众人俯身查看,果然发现细微缺陷。重新调整振捣点位后,混凝土终于如绸缎般均匀流淌。日出时分,首个“巨无霸”T梁在晨光中揭开面纱,技术人员相拥而庆。
这个夜晚开启了一场持续22个月的预制马拉松。990片T梁在小村预制场诞生,每片都需要经过8道质检关卡。张拉工何庆功记得最清楚:“预应力钢绞线的张拉控制就像给巨人系鞋带一样,力大了会断,力小了会松。”
两洞桥大桥的施工场景更为惊心动魄。站在谷底仰望,陡峭的崖壁仿佛被巨斧劈开,主墩位置竟是百米虚空。技术团队创造的“悬空筑台”法,让现代工程技术与远古的鹰筑巢智慧不相而谋。
青年突击队员罗林芝系着双保险安全绳,在距谷底128米的高空绑扎钢筋。山风穿透工装,在他年轻的脸庞上刻下红痕。“第一次上来时腿抖得站不住,”他笑着说,“但现在我能在这跳华尔兹。”问及恐惧,他望向远处村庄:“怕!但想到老乡们再不用绕三小时山路,手就稳了。”
400平方米的空中作业平台由崖壁钻孔植入的钢桁架支撑,工人们在上面焊接、浇筑、吊装,完成着看似不可能的施工任务。项目经理谭小艺形容这是“在刀锋上跳舞”,每个焊点都关系着整座大桥的安危。
架梁过程更是一场空中芭蕾。峡谷瞬时强风可达6级以上,吊装中的梁体会像钟摆一样晃动。狭窄场地限制了大中型机械施展身手,建设者创新采用“跨墩提梁”方案——在桥墩间架设专用提梁机,将T梁垂直提升至桥面。
“就像用筷子夹豆腐,既要稳又要准。”起重指挥老刘这样形容。他的指挥旗语精准如乐队指挥,每片T梁下落时,技术员任佳辉要用全站仪进行三次坐标复核。有时为了等待合适的风力窗口,团队要在现场守候数小时。
炮车在峡谷中轰鸣,最后一批T梁吊装时,村支书姚安全站在对面山头久久凝望。这位当了二十年的老支书掏出手机,对着初具雏形的桥面连拍数张:“等高速通了,山里的花生、药材当天就能运到武汉。”
如今,已完成架设的T梁如一组巨大的钢铁琴键,于深谷中鸣奏建设交响曲。四标段工程图上92%的进度标记格外醒目,但建设者们不敢有丝毫松懈——还有桥面铺装、防撞护栏、沥青铺设等工序在等待。
晚霞绚烂,焊花如星光般在峡谷间闪烁。董吉勇副经理翻开施工日志,在“洞湾1号大桥右幅贯通”条目后郑重签下名字。远处,建设者的宿营地亮起灯火,与夜空星辰交相辉映。
这些筑路人在群山间编织着天路经纬,用毫米级的精度改写着重峦叠嶂的交通命运。每片T梁落位的铿锵声,都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鼓点,在这片曾经被大山封锁的土地上,敲响着新时代的回音。
路连民心:一条大道的山乡蝶变
2025年8月的清晨,李子溪的薄雾尚未散尽,利咸高速小村互通工地已响起金属碰撞的交响。钢筋丛林间,80多名工人在40米高空如履平地,焊枪喷射的蓝焰与初升的朝阳交相辉映。中交二航局项目副经理董吉勇的安全帽下渗出细汗,他的目光掠过正在浇筑的C、E匝道:“每1米混凝土都要经受千年地质考验。”
300米外,洞湾1号大桥工地上,技术员任佳辉仰头凝视架桥机吊起的第100片T梁。这个28岁的甘肃小伙儿在本子上记录:“梁体编号LX100-7,竖向偏差1.3毫米,低于国标2毫米限值。”阳光在97吨重的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上折射,在他黝黑的脸庞上切出明暗交界线——这是无数个昼夜坚守刻下的勋章。
县高速公路建设服务中心的墙面被巨型路线图占据,主任贺方亮的激光笔在等高线间游走:“利川至咸丰直线距离仅60公里,但武陵山余脉就像被巨神揉皱的绿绸。”红色标记沿着北纬30°艰难延伸,在沙盘上划出惊人的86%桥隧比曲线。他停顿时手指微颤:“不是缩短1.5小时车程,是重塑武陵山区的时空坐标系。”
五座贯通隧道如巨兽蛰伏山腹,两洞桥大桥合龙段似银链悬空。测量队的全站仪终日闪烁,将北斗卫星的坐标转化为桥墩的精准落点。在北斗系统支撑下,建设者攻克了5处深切峡谷和7处滑坡点,让路线纵坡始终控制在5%以内——这是满载茶叶的货车能安全通行的极限坡度。
山坡上看施工的村民越来越多。老人抱着孙儿指点云间的桥墩:“以后你去城里读书,汽车在云里飞哩。”孩子数着架桥机吊装的梁片,把数到的数字写进作文——《我家乡的彩虹》。
夕阳给洞湾1号大桥镀上金边时,建设者们悄然退场。假以时日,1号搅拌站将转型为茶叶加工厂,施工便道将硬化成产业路。唯有桥墩上的水准点标记诉说着来路——那是建设者留给大山的备忘录。
试想,在2026年某一天的晨光中,第一辆满载茶箱的冷链车驶上马河特大桥,山风掠过云海茶山。驾驶员手机导航显示:距武汉市区520公里,预计抵达时间5小时17分。包装盒上咸丰白茶的新标签——“唐崖云端茶·海拔1200米高速直达”,格外醒目。
在山脉的寂静深处,194.5亿元投资正转化为另一种存在形式:茶商微信群里不断刷新的订单提示音,药材合作社新安装的真空包装机的轰鸣声,还有与留守儿童视频通话时“爸爸,过年就从高速回家喽”的清脆童声。
当北斗卫星掠过北纬30°上空,利咸高速在遥感影像上化作银线串珠。那些最大埋深达430米的隧道群、主跨1000米的连续高架桥,不仅是交通史上的工程样本,更成为刻录在鄂西南腹地的年轮——记录着从地理褶皱到经济高地的蜕变史诗。
此刻,茶园里悄然生长的茶苗正将根系探向路基深处,仿佛要触摸这场蝶变的温度。而大山记得:曾有群戴安全帽的造梦者,用5万吨钢筋和100万方混凝土,为四标段跨越的几个乡镇40万人种下了穿越时空的彩虹。
尾声:丰碑矗立,大道如歌
小村互通初具雏形,五座隧道尽数贯通,标段进度已达92%。这条曾经只存在于蓝图上的曲线,终于以不可阻挡的姿态,深深嵌入错落山川的肌理,将天堑化为坦荡通途。
万壑间,利咸高速如一条蓄势待发的巨龙,正将昔日的天堑一寸寸锻造成通途。它承载的,岂止是车轮的速度?那更是无数建设者以热血为墨、以山川为卷,用实干、匠心、智慧、绿色、和谐与忠诚共同挥毫写就的壮丽诗行。当第一辆车驶上这崭新的坦途,呼啸而过的风声里,必将久久回荡着建设者不屈的号子与大山深处那如雷的、奔向未来的澎湃心跳——千峰俯首处,大道终如虹。
这条穿行于北纬30°神秘地带的天路,不仅是钢筋混凝土的造物,更是建设者以勇气重绘山河的史诗。当未来车辆疾驰而过,崖壁上59公里便道的残迹,将如勋章般诉说:所有不可逾越的天堑,终将在人类的意志前臣服。
它是一座无言的丰碑。其碑文,铭刻在每一根深入岩层的桩基上,在每一块严丝合缝的预制梁里,在每一米平整坚实的路面上。这是用钢铁意志铸就、用智慧汗水浇筑、用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数次跌倒爬起换来的现代工程标杆。
它还是一座血肉铸就的群像丰碑。那些被阳光晒脱了皮的脸庞,那些被机油和泥浆染透的工装,那些在图纸前紧锁的眉头,那些在协调中磨破的嘴皮,那些为了通路而让出的祖屋和田地……每一个身影,每一个名字,即使未被一一记载,都是这座丰碑上最鲜活、最动人的浮雕。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却是真正的脊梁。他们的故事,是天堑变通途最核心的灵魂。
它更是一帧时代的剪影。李子溪,这个曾经偏居一隅的小山村,因为这条路的贯穿,被历史性地推向了开放发展的前沿。引擎声唤醒了千年的沉寂,山外的风潮正沿着崭新的路面汹涌而来。这剪影里,有老农第一次坐上便捷大巴出山时的局促与新奇,有返乡青年看着物流货车直通家门口时的兴奋筹划,有孩童沿着崭新人行道奔向更远学校的轻快脚步……李子溪的奋进新篇,已然随着车轮的飞转,翻开了充满希望的第一页。
大道如歌,声震群山。这歌声,是筑路者铁锤与机械的铿锵交响,是通车后车流不息的呼啸长鸣,更是世代山民梦想成真后,从心底流淌出的、最深沉最欢畅的和鸣。这歌声所吟唱的,不仅仅是一段路的诞生史,更是一个地区冲破地理桎梏、拥抱时代浪潮的觉醒史与奋斗史。它将是小村,以及所有被这条高速路所改变的城镇乡村,迈向更加广阔未来时,最忠实、最厚重的见证。
山河为证,此路已成。通途之上,未来已来。
来源:《唐崖》2025年·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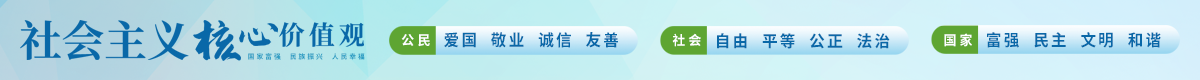






精彩评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请遵守评论服务协议
共0条评论